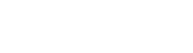这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疫情,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疫病大流行总会过去,但是它带来的影响,会不会根本性地改变我们的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呢?
丨曾经的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了
从中美建交至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中美科技关系总体上是相互合作的态势。1979年1月,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奠定了两国科技合作的基础。据统计,双方在《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涉及农业、商务、国防、能源、卫生、教育、核工业等领域。1979年至1989年期间,两国在核技术、高能物理、军工等一些敏感领域的合作有所突破。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民间领域的科技合作显著加强了。美国科技公司将产品生产和组装环节外包给中国的供应商,催生了中国本土科技产业的发展。中美两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美国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外观设计、品牌营销和关键零部件供应,中国企业主导组装和低端零部件供应的产业合作链条。
在中国组装生产的科技产品运回到美国本土,再通过美国公司的销售网络分销到全球。为了进一步开发中国市场,美国科技公司在中国设立大量研发中心。这些中心既为公司总部的项目服务,又指导公司在中国产业链的发展。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国科技企业也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全球科技市场的迅速膨胀,促成了大量中国科研人员赴美深造,以及中美科技领域相互投资。
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中美科技领域的部分矛盾开始显现。就拿光伏产业来说,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及就业,美国在2012年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反补贴关税。中国也对美国采取了对应的贸易反制措施,并且鼓励国内市场吸纳中国光伏产能。从最终结果看,中美在光伏上的贸易战并没有改变光伏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整体趋势,反而加速了美国光伏原材料产业的衰落。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歧也显著增加。从2018年的中兴事件、2019年的华为事件,后来愈演愈烈的贸易战,美国就开始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
2020年这次新冠疫情,似乎成了中美脱钩的催化剂。双方的不信任开始加剧。中国制造的KN95口罩,被美国检测出低劣产品过多,质量不合格,被美国FDA整体移出了口罩供应商。
随着新冠在美国的大规模爆发,在美国的一些人包括政治人物毫无道理地把新冠病毒“种族主义化”之后,我们持续听到有许多政客在指责中国,称中国没有在早期及时作出响应或没有进行充分检测。此外还有要求中国赔款:3月17日,美国保守派官员Larry Klayman要求中国政府为冠状病毒带来的损失赔偿20万亿美元;4月6日,英国某外交智库向中国政府追讨3,510亿英镑的赔偿金;澳大利亚参议员Alex Antic要求赔偿金赔偿金约为5088亿美元。这种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如今仍在继续,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恶劣影响。
在产业层面,当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时候,美国加快了对全球产业链里中国高科技企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打击力度。在美国有政客说,美国政府要加快制造业回归美国。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建议,如果美国政府的条件允许的话,他希望给予从中国迁回去的美国企业相当大的搬迁优惠力度。
因为此次抗疫过程中出现的许多资源短缺问题,全球的相关产业链可能会有相当大的重组、调整。有相当多的产业或加速撤离中国。“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容易引起欧美的警惕和反制措施,英国《经济学人》在《隔离之下的全球化》中就指出这点,认为这是新冠病毒带给世界的严厉教训,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世界对中国依赖的警惕仍会加重。
丨制造链向外转移,经济加速“脱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看来,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封城、封国,阻断人流物流,阻断交通运输,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后果。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全球化风险?
不过,也有不少分析认为,全球分工的加深,尤其是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高效,已让世界离不开中国。最近在金融投资界流传的摩根士丹利观点便是典型:
中美关系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在疫情初期,尽管美国政府并未对华援助,美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普通美国人都为中国抗疫提供了众多帮助。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的科学家与医生从1月起到现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最近,随着美国面临着新冠危机的挑战,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中国企业,都在不停地为美国提供帮助。这种积极的发展确实为双边关系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合作超越了地缘政治。
这次危机发生在中美政治关系的低谷期,双边在危机的早期未能很好合作,但是双方最终都意识到:我们必须合作、我们可以合作。
另外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叫的最厉害的是美国的政客,而他们的呼声并未得到企业的一致性回应。在“峰瑞资本”的公众号上有一篇文章,从苹果、特斯拉、GE、3M 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博弈看,美国政府说什么,对企业的影响较小。有意思的是,当政府意志与企业目标相悖时,政府选择了维护企业利益。
产业是逐利的。受政治影响小,受民众情绪影响也小。分布在各个产业链的各国企业,通过自发的协作、共建生态,实现利益最大化、效率更优,是最明智的做法。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认为,一个产业链集群基地的形成将是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自主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国家政府行政管制的结果。
丨未来全球化的新秩序
毫无疑问,疫情过后,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世界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认为,“新冠前后”将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因为疫情,世界会划分为2020年前和2020年后两个纪元。
病毒带给的痛苦,人们一定会部分地选择遗忘,这也是人的一种心理修复机制;但有些事又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从长远讲,它们一定会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到人们的认知与行为。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认为,疫情会对运行了几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产生颠覆性影响,但它不会终结全球化,而是会重塑全球化的形态。这次疫情则彻底暴露了这一弊端,让全球化的旧模式走到了尽头。但人类社会不会回到全球化进程之前的各国各自为政、主权至上、奉行重商主义的老格局上。人类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和知识观念,未来还是会在全球范围里交往和流通,任何一个国家离开全球化都不能独自发展,人类肯定会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这是摆脱不了的必然趋势。
因此,面对这个全新的、提高了门槛的全球化,中国有两个选择,要么实实在在地推进体制改革,融入那个自由经济共同体,要么闭关自守,这意味着切断和外界联系,中国人生活水准大幅降低,中国的技术迭代能力跟不上,中国经济最终止步不前。这个代价我们能否承受?
高全喜教授认为,旧的全球化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新的全球化跟旧秩序的不同点,要从这三个因素来看:
从这三个因素来看,新全球化提高了门槛,靠走捷径、搭便车的红利是肯定行不通了。这个新的世界,它坚守自己的标准,抑制住投机者的贪婪,同时维持开放性,提倡世界的真诚交流与合作,让那些愿意真正参与全球化的人加入。
每一位「全球风口」的读者都应该为这个未来的新全球化做好准备,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变革自己,向那个未来的新世界靠拢。
全球科技投资人王煜全在最新的讲座《全球会进入大萧条吗》中提到,疫情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融入全球经济的最佳时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走出去做全球化的布局,这种全球化布局不应该是其他国家的人来做,应该是最懂供应链、最懂产业链的人来做,是谁呢?是中国人。具体的操作方法,王煜全会在“科技特训营特别版”——线上书院中详细分享,旨在培养能够融入全球创新生态的企业家。